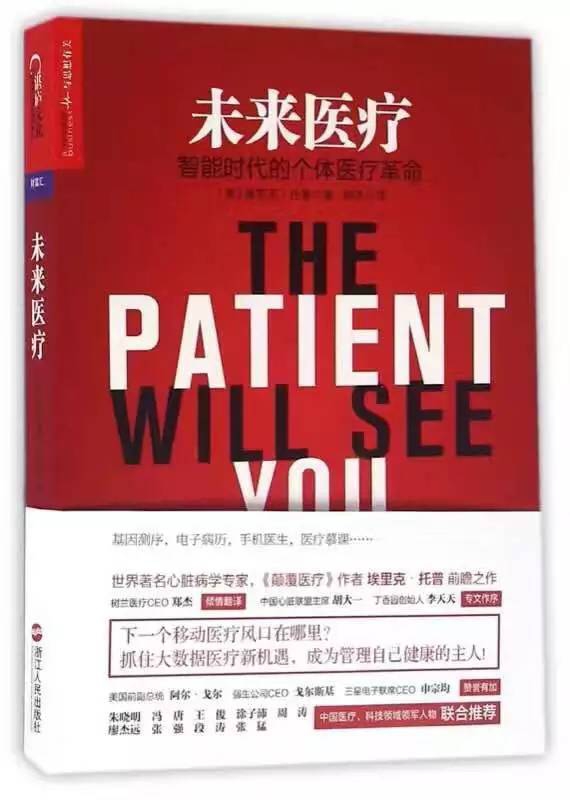
小编语:在传统医学中面对疾病,患者总是被动接受。而在大数据开启的智能时代下,医疗领域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民主医疗时代即将到来。“下一个移动医疗风口在哪里?抓住大数据医疗新机遇,成为管理自己健康的主人!”《未来医疗》一面世就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相信不同的人看了这本书都有自己不同的感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副主任、脊柱外科主任梁裕教授给我们平台赐稿一篇,分享他作为医生看完这本书的感想。
正 文
一、前言
医学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对医学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也前所未有地有力和迅捷。例如,从伽利略发明显微镜,到外科手术中应用显微镜,中间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军事领域中全球定位(GPS)运用到外科手术中的计算机导航,中间只花了区区20多年。从我从事的脊柱外科领域来说,公认的发展方向是微创脊柱外科,节段保留技术,计算机导航和机器人技术以及脊柱的生物学治疗,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脱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存在和发展。
仅仅是医学技术上的进步就足以使忙忙碌碌的医生们疲于应对,但现实是,医学的发展既依赖于科技的进步,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民主化早已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炙手可热的术语,而美国著名心脏医生Eric Topol的《未来医疗》为我们描绘了医学和医患关系未来走向的生动画卷,正是医疗的民主化。具体来说,就是从医生权威主导的医疗模式向病人充分知情并深度参与的平等民主的医疗过程的转变。
二、医疗模式改变的必要性
古希腊以降,医学和医患关系的基本形态从来不曾改变。那就是由医生主导的医疗行为和医疗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形态下,医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上帝的使者(白衣天使)的角色出现。Topol指出,希波克拉底被誉为“医学之父”,但他同时也是“家长式的医学之父“。因为他认为:医生应该向病人隐瞒病情,包括病人未来或当前的情况。他坚信不应该让病人知道诊疗处方,只有医生群体才能掌握医疗知识。希波克拉底建立的医学模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强化。杰伊.卡茨总结道,传统的医患关系是,病人必须尊重医生,因为医生的权威来自上帝;患者必须对他们的医生有信心;患者必须服从医生。不可否认,传统的医疗模式对治疗疾病,缓解痛苦,改善人类健康方面居功至伟,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家长式的医疗模式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由于病人对于自身的疾病所知甚少,对治疗方法的利弊不知其详,客观上损害了患者自身的利益和选择的权利。例如,我国的一些民营医疗机构推荐PET-CT作为年度体检的常规项目,作为早期诊断肿瘤的筛选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被告知,这类核医学检查的每次辐射剂量大约为40mSv,等同于进行2000次胸片的辐射量。美国虽然在1957年就推出了医疗知情同意制度,但这一告知常常流于形式,文书规定,不管遭遇任何不幸的手术结果,你都放弃一切起诉医生的权利。虽然在客观上,这种知情同意有“霸王条款”之嫌,但很少有病人会拒绝签名而放弃治疗。信息和地位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医疗关系中施者和受者的不平等性。在治疗结果满意时,这一切都被掩盖,而当治疗结果差强人意时,这些对于医疗关系结构的不满可能爆发出来。因此,传统医疗模式的弊端是对于医患双方的损害。我国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伤医和杀医的恶性事件,固然与国家的医疗体制和舆论的导向有关,但与家长式的医疗模式也不无关系。根据Topol的定义,新的医学模式下的“患者”,应当指的是积极参与自身治疗,争取博得与医生同等的尊敬,对自身所有医疗数据都知情的人。
三、医疗模式改变的必然性
应该指出,Eric Topol不仅仅是一个在专业领域里建树颇丰、声名远播的心脏科专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邃洞察力,具有良好社会学和政治学素养的杂家。他敏锐地指出,医学模式改变的可能性是基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事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某种程度上基于信息载体的革命。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以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极为昂贵,如竹简、羊皮和青铜器等,通常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在欧洲,仅占总人群的8%)。民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模式是聆听。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模式从听觉模式向视觉模式转换,印刷本数量猛增,成本急剧下降,公众对书籍的可及性大大提高,很快有大量的普通人群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回顾整个印刷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的一系列改变。机印书推动了宗教改革、第一次工业革命、超过10次的宗教战争和文艺复兴等。Topol进一步认为,始于1440年的通信革命(以古登堡印刷机为标志)在今天再度上演,只不过今天,信息的载体变成了基于互联网的智能设备。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创新的时时涌现,个人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五花八门的移动智能设备已成为所有人社交的工具,使社交变得轻而易举,大家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传播知识和信息,成本大幅下降,打破了国家及地域的界限和屏障。移动智能设备和印刷术在信息共享上竟然是如此地相似。他乐观地认为,我们将要看到一场由移动智能设备带来的医学革命,医疗信息流也将要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曾经一贯的以医生先掌握数据再慢慢让患者看到的模式会被取代,这种以怀揣秘籍保持权威的行事方式将被完全颠覆。
四、如何面对医疗模式的改变
Topol展望了信息革命及移动智能设备可能给医疗模式带来的改变,他认为数据革命将成就个体化医疗。公众将拥有自己的人体GIS(医疗数据信息系统),包括全基因序列、传感器数据、医疗记录、扫描影像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GIS信息做出重要的医疗选择,并根据情况和需要订制个体化的医疗方案。面对已经和即将到来的改变,基于传统医学教育体系培养的医疗从业者应该如何认识和应对,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家长式的医疗模式中医生更有话语权。家长式的医疗模式中医者的权威决定了医疗行为的效率。医生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下,更习惯于一言九鼎,不容病人置喙。同行中就有将“十万个为什么”的患者列入不宜手术名单的潜规则。所谓“专家暴政”是有快感的,相信大多数医者会对此恋恋不舍,一旦被剥夺,无疑是痛苦的。就像在历史上,独裁者主动放弃独裁者微乎其微。要应对正在来临的医学模式改变,我认为以下几点尤其值得重视:
1.重视客户导向
应该看到,无论你接受还是抗拒,医疗模式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深刻的改变。改变是绝对的,不改变是相对的。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手术病人都比较在乎切口的大小。瑞金医院的外科理念传统上主张大切口。在我做实习医生时,上级医生告诉我,切口一定要足够大,否则术中看不清重要的血管神经,会增加病人的不必要损伤的风险。这种判断,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无疑是正确的。但三十多年来,手术病人一如既往地在乎切口的大小,他们会互相比较切口大小,计算缝针的多少。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开展,如内镜技术、显微技术、机器人以及计算机导航技术等,手术的微创化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发展的趋势之一,小切口不再意味着看不清楚,通过小小的钥匙孔大小的切口,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过去需要巨大切口才能完成的手术。就一胆囊切除术来说,腹腔镜手术已经深入人心,臻于成熟,如今如果你仍然拒绝微创技术,坚持让病人接受切开手术,毫无疑问,你便会失去你的客户-病人。
2.调整医者角色
医疗模式的民主化,决定了医疗行为不再是医者的单向施与,而是医患的共同参与。医者要学会做合作者。要做好一个合作者,就要容忍并且习惯病人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学会接受病人对你的专业知识的质疑和挑战;要做好一个合作者,更需要医者具有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心胸,认识到仅仅依靠自己单方面的学养和专业知识,未必能得出最佳的诊断和治疗的结果。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病家诉求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在美国,病人也具有创新精神。经常有病人拿着从网络上得到的新技术信息,对医生说,我要做这个最新的手术。而在国内,病人往往会询问病人,你之前做过多少这样的手术,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业已成熟开展的手术术式。在民主化的医疗模式下,充分倾听病人的诉求,乐见病人的参与,并根据不同的病情,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背景开展个体化的医疗,是医者的必然出路。
3.不断学习进取
如前所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将逐渐填平医患之间的知识鸿沟,原先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也将逐渐消弭。丰富的专业知识已经不是医者的专利。这就对医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变得同等重要。做一个好医生,当然要有博大的人文情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设备正成为全社会重要的学习途径,不能想象,一个不懂基本网络知识、不懂如何操作智能手机的医生如何在新的医疗模式下生存。在“专家暴政”的模式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的专业权威一般很少受到挑战,而在未来,医生面临的学习任务会更重。医生只有不断时时掌握更新更多的相关疾病信息及各类新技术的运用知识,才可能完美应对可能的挑战,提出准确的临床意见和观点,赢得病家的信任。
我们应该具备必要的洞察力和宏观思考,积极应对在变化中医疗模式下医生的角色和作用,以期在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应付裕如,避免进退失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临床医生都有读一读这本《未来医学》的必要。
作 者:梁 裕
责任编辑:余可谊
美术编辑:黄付敏